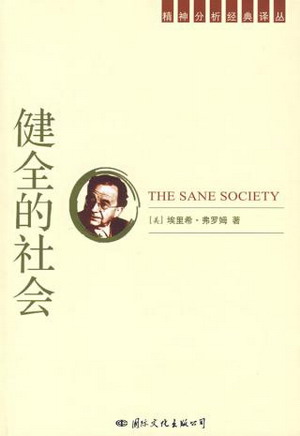 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结尾,弗洛伊德指出,既然文明能使人发神经,而社会又是由人所组成,作用于人的各文明戒律同样作用于社会,那么显然社会也可能陷入病态。但他也坦陈“自己对这个难题的逻辑和方法论的障碍心存
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结尾,弗洛伊德指出,既然文明能使人发神经,而社会又是由人所组成,作用于人的各文明戒律同样作用于社会,那么显然社会也可能陷入病态。但他也坦陈“自己对这个难题的逻辑和方法论的障碍心存
弗罗姆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从1940年代开始,弗罗姆先后发表了《逃避自由》《自私的人》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揭露了资本社会中人的存在困境,而对“文化”、对人的存在困境的质询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合理性提出质疑。《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发表于1955年,尽管时隔半个世纪,但正如大卫・英格莱比给该书1991年伦敦增订版所作的导言宣称的那样,“尽管本书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暂时的,但其写作方式却绝不是。它不仅是弗罗姆为我们这个文明的疾患提出的补救办法,而且它首先提出了一种关于救治方法的观念。”
一、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我们的精神是健全的吗?”弗罗姆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以众多的事例来佐证:历史上签订了无数个和平条约,可人类却有无数次的相互屠戮;在经济体制当中,一场非常好的收成往往也是一场经济灾难;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却不知如何使用;以及自杀、杀人与酗酒等众多现象的普遍化反映出了人的精神的剧烈撕裂。这些都是病态社会的征兆。
那么,何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病呢?弗罗姆认为,首先得看整个社会的人是否普遍地处于一种病态化的存在状态之中。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对人的压抑后果的理论早已解释了这一点,即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现神经病,然而普遍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模式的病态化和大量存在的精神病患者都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一定出了问题。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弗罗姆探讨了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社会常态病理。这也是该书整个思想的前提。一个真正的“人的科学”将确立人类本质的性质,将使我们区分“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方法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令人满意的,哪些是令人不满意的”。弗罗姆建议对人类的本性进行研究――这个本性“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核心”,并把它作为衡量所有不同社会的心理健康的标准。
弗罗姆要解决的第一个任务是进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确定什么是人性,以及由这一人性引发的需求是什么”。它以人作为目的和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其价值判断并非从人的生物禀赋出发。因此,人的尊严、人的生产性本性是一切社会统治、管理形式必须遵循的标准。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病的客观标准只能由人来确定,即看人在这个特定社会中的命运。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病态;几乎所有社会都有使人致病的诸多社会因素,它们都有权力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共同点,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劳动的剥夺和意识形态的奴役就表明这是社会的病态。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不同之处,不过是把对人的操纵、奴役隐秘化了,人的主体性被彻底“消解”,人的精神世界危机四伏。
由此,弗罗姆确立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尺度,便是它不符合人性和人的需要。人自动地以其全部生活嵌入到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之中,附属于原本由其自身所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处于任何一种文化中的人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独特的外表却是由其所居住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比如人的攻击性和贪婪,与其说是人性,不如说是人的生命受挫和精神发展出现障碍的结果,它们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因为人只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确认。通过人的病态行为和对他们在致病环境中的反应,可以反向推出人性的某种内涵。这就是说,抽象的人性只有从人对具体社会环境产生的某种反应上才能理解。
通过对人的反应形式的考察,弗罗姆认为:人如果不是天生的精神或道德上的白痴,都力求活得幸福、健康、有活力,能发挥出他的生命潜能。这就是说,人渴望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与他人和谐相处,在自由的基础上有尊严、健康地生活。这与那种认为人性本恶、人性自私的看法截然不同。而实际上,后者的“实然状态”并不是“人性”,而是人性被后天的社会环境所摧残、扭曲变形后的结果。
与人性一样,人的需要在社会中也遭到了扭曲。我们所看到的需要不代表人的本真渴求,而是社会所强加的结果。这正如弗罗姆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的:“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这里所说的需要不一定是他自己认为的需要,因为最病态的目标也能够被人主观上认为是最需要的东西。这里所说的需要是指客观的,可以通过人们的研究确定下来。”
弗罗姆所论述的需要有别于人的植根于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的需要,也不同于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需要理论。他总结了五种需要:交往的需要(need for relatedness),指个体具有爱他人与被爱的需求;超越的需要(need for transcendence),指个人希望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在精神上能表现出创造性的人格特质;寻根的需要(need for rootedness),指个人希望与他人、社会以及大自然亲密结合,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需求;身份认同的需要(need for identity),指个人力求获得完整人格,希望活出意义的心理倾向;定向需要(need for a frame of orientation),指个人具有努力寻求生活方向从而得到心安的心理倾向。它们是人的“内在需要”,只要是人,都必须解决这些需要,否则在心理上他将无法生存下去。也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和个人都有解决这些需要的方式。
弗罗姆也分析了解决不同需要的矛盾性,如对于交往需要存在着社会合群性和自闭性两种可能;超越的需要面临着创造力和破坏力两种形式;满足寻根需要的方式可能获得友爱,也可能陷入乱伦的幻想――回到子宫和大地;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个体和群体一致性的对立;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满足定向需要的理性与非理性方式的对立。然而悲剧在于,一方面,理性的方式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逃避途径,它只能导致普遍的屈从和奴役;另一方面,那些“有勇气”选择非理性方式的少数人,也被社会的理性及其统治功能阻断了进路。
二、社会病理的诊断
人的需要是弗罗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点,而“异化”这个概念则是他理论的中心。这个由马克思提出,经过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强化的概念,成了弗罗姆理论要旨最集中的表达。这是一个既有事实判断又有价值判断的术语,它将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工人阶级被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图景,置换成了人在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机器体系的操纵下彻底失去“人性”而物化的素描。它是一种解释社会病态行为的观念模式。一切有违人的本性的非正常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异化,因而都具有病理学特征。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性格是“竞争、囤积、剥削、崇拜权威、攻击性、个人主义”,那么,“异化”概念所具有的“20世纪特征”概括了人类的命运,并在无数社会批判者的手里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的秘密”。
人的异化是一种与文明伴生的现象。所谓异化,指的便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相分离并转而对人构成否定。异化首先表现为人的生存需要与内心诉求的分裂。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去工作,首先便必须经历两重异化。一是服从于管理者或雇主,以付出人格尊严的代价谋得一碗饭吃。二是必须将自己当成机器本身的一颗螺丝融入生产的机器体系之中。现代生产体系建立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只能在微不足道的岗位上从事工作,对整个生产进程相当隔膜。个人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被带入生产进程中随着机器体系而运转,这就极大地破坏了人的理性。与此相对,管理者也在异化中苦苦挣扎。管理人员不直接面对机器体系,却面对着竞争的企业、庞大的市场、抽象的消费者和其他强大的社会组织。这些庞然大物都代表了一种不可捉摸的非理性力量而时时控制住管理者的思想和感情。在官僚化统治和管理中,官僚们更是一些既无爱也无恨的管理机器。他们像统治管理数字、物品、机器一样地操纵和役使被统治者、被管理者,自身也在这种统治和管理中物化了。
最悄无声息的是消费的异化。消费本是人为了获得生存和享受,由感觉、爱好、审美等因素参与的一种具体行为,然而现代消费追求的却是最大化的原则,人们只要求占有,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空虚。消费已经与人的真实需要失去了联系,成了一种目的。
人的异化不仅有与世界、他人的异化,更有与自己的异化:“人与自身的关系如何呢?我在别处把这种关系描述为‘买卖倾向’。在这种倾向中,人体验到自身是一个能够在市场上被人们成功利用的东西。人并不把自身看作是自身权利的持有者,一个积极的作用者,他的目标是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自己……”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异化,将人的存在置于一种虚幻的物化支点上。这确实是“人的死亡”。
三、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通往精神健全之路”
弗罗姆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并不像韦伯那样,认为人类发展到最后注定受无法逃避“铁笼”的束缚。在英格莱比看来,弗罗姆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他相信对人类疾患的诊断可以基于“究竟什么是人”的客观定义来进行。他像哈贝马斯那样宣称:人类根本没有死亡,只是尚未成年。
弗罗姆检视了各种社会诊治方案:极权主义的偶像崇拜、超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目的即为揭示人的需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弗罗姆点到为止(精彩而详尽的分析可参见其《逃避自由》一书),认为它们从纯粹意义上说,是病理学的,是一种对人的发展早期阶段的回归――是婴儿般的对非理性权威的依赖,是“逃离自由”又奔向新的领袖和国家的偶像崇拜。超级资本主义,是一种与极权主义截然不同的解决工业问题的方案,由美、法等国的工业家所提出,其实质是通过刺激性管理、利润分享制度,让工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参与者,从而消除了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
弗罗姆更多地是吸收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而认为其晚年的思想中有极权主义的种子。但英格莱比也指出,弗罗姆并未能“将莫斯科型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分开”。既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营造出的是一个病态的非人道社会,那么相应的方案只能是用一个符合人真正需要,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来取代。在分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中的实际变化的种种可能性之后,弗罗姆认为,仅仅在一个层面的变革注定是非建设性的。基督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都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有当工业和政治的体质、精神和哲学的倾向、性格结构以及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化,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只注重一个领域的变化,而排除或忽视其它领域的变化,不会产生整体的变化。事实上,这似乎正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只有对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结构全面地进行改造,才有可能终结异化,消除社会的病态。因为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复杂地、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任何一个领域都受到其他领域的干扰甚至支配。这显然是一种从马克思、卢卡奇那里继承过来的“总体化思想”。
因此,没有一个现存的社会建设或诊治方案能让弗罗姆满意,只有对社会-心理关系给予了政治或经济同等重视的“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获得了弗罗姆的好感。这一概念是弗罗姆从马克思主义那儿演变来的,并阐释为共享工作、共享经验、共同管理的人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另一个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是中心,而所有的政治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那就是:终结人的异化状态,将人从被各种异化实体和力量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全面改造社会,克服生产单向度化导致的人的残缺不全,恢复人健全的理性,使人能全面发展;确立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摆脱物对人的占有和支配;建立起一个以爱为宗旨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四、一种乌托邦?
弗罗姆否认,但他的设想未必不是一种“现代的乌托邦”。因为,社会结构的全面变动注定不可能,而单方面的变动则极易受到其他领域的渗透而陷于失败。他所设计的“健全的社会”之所以具有乌托邦性质,在于其本质上是按理想的人的形象来对社会进行设计,这种采取与现实社会性质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进行的理性设计,越是精巧越会沦为一种乌托邦。
曼海姆说,乌托邦是“明天的现实”,它的超越性维度和强烈的批判色彩恰恰是任何一种与为现状辩护彻底决裂的批判理论所需要的。因此,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弗罗姆设想的“健全社会”具有的乌托邦表征,恰恰是人内心未灭的解放的渴望。乌托邦可以用来比照社会现实,从而揭露出后者的残缺并促其改变。
(《健全的社会》,埃里希・弗罗姆著,蒋重跃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3月版,32.00元)
(本文编辑:李焱)
